她已经不会再为了他们父子俩伤心难过了。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她去关心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,她刚收到消息,前几年资助的三个学生考上了大学,要来谢家看她。资助用的是她自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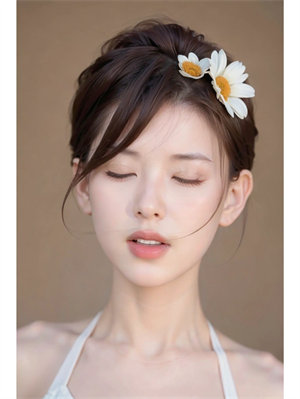
她已经不会再为了他们父子俩伤心难过了。
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她去关心。
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,她刚收到消息,前几年资助的三个学生考上了大学,要来谢家看她。
资助用的是她自己的钱。
她好开心,能帮助别人她觉得很幸福。
温晗芯将最后一颗芒果摆在蛋糕上时,听见了前院的喧哗声。
她擦了擦手,看见三个穿着朴素的大学生站在客厅里,手里捧着皱巴巴的感谢信。
质朴纯真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别的情感。
领头的男孩紧张地捏着洗得发白的衣角,“温姐姐,我们考上B大了。”
太好了,终于苦尽甘来。
温晗芯真心为他们感到开心。
可是,总有人要在这个快乐的日子找不痛快。
凌清菀牵着谢念的手走进来,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,“晗芯姐在开茶话会啊?希望别嫌弃我们不请自来。”
来都来了,总不能赶她走吧。
温晗芯没说话,只是将蛋糕往学生们面前推了推,“尝尝,我自己烤的。”
学生们都很害羞。
连连道谢,眼神中都是清澈和感恩。
谢念突然挣脱凌清菀的手,冲到蛋糕前,“我也要吃!”
一块蛋糕而已,平时什么样的蛋糕没有?
非得来这里插一句嘴。
“念儿别急。”凌清菀从侍者手里接过一杯冰水。
给孩子冰水干什么?
温晗芯看见谢念眼睛一亮,孩子接过了那杯冰水,她太熟悉这个表情了,每次恶作剧前,谢念都会这样笑。
冰水当头浇下时,奶油花朵瞬间坍塌。
学生们惊慌地站起来,却没人乱说话,甚至向温晗芯投去担忧的目光,确定她没事才低下了头。
他们很不安。
害怕是他们的到来,惹得别人不舒服。
愧疚的心情包围着学生们。
芒果顺着桌沿滚落,在米色地毯上留下几道醒目的红痕。
谢逸亭就是在这时走进来的。
佛珠缠在腕间,一身西装革履,像是刚从重要会议回来,他目光扫过一片狼藉的餐桌,最后落在温晗芯身上。
温晗芯没有擦脸上的水渍。
她只是轻轻放下沾满奶油的蛋糕刀,将被浸湿的感谢信一张张摊开在茶几上晾干。
动作很慢,很仔细。
“逸亭哥,念儿不是故意的。”凌清菀娇声道,故意不咸不淡地解释,“小孩子贪玩嘛。”
真的不是故意的吗?
品性能投射在一言一行里,通过日常小事表现出来。
恶种远比善意来得简单直接。
谢念躲到凌清菀身后,露出半张脸,“爸爸,我只是想帮蛋糕降温。”
小孩子的做法,有一些来自于大人的授意。
意图毁坏她的一切,是谁的想法不用琢磨就知道。
温晗芯突然笑了。
她抬头看向谢逸亭,水珠顺着她的睫毛往下滴,像是眼泪,又不是。
对面谢逸亭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。
他记得上次谢念打碎古董花瓶时,温晗芯红着眼睛求他别罚孩子,小时候谢念抓伤她的脸,她也是第一时间护住孩子说“不疼”。
可现在。
她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,连睫毛都没颤一下。
“道歉。”谢逸亭突然说。
凌清菀笑容僵在脸上,“逸亭哥,孩子还小。”
“念儿。”谢逸亭加重语气,“道歉。”
弹幕已经无语了。
他终于长眼了?
除了温晗芯和学生们,这里的人都是神经。
谢念瘪着嘴,不情不愿地说了句“对不起”。
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
温晗芯点点头,转身对三个手足无措的学生说,“我带你们去换衣服。”
她经过谢逸亭身边时,闻到了熟悉的檀香味。
只觉得陌生又恶心。
“晗芯。”谢逸亭突然抓住她的手腕,想要说些什么,“你......”
怎么不哭不闹?
为什么看向他们的眼神突然好陌生?
温晗芯轻轻抽出手,“蛋糕还有材料,我再去做一个。”
佛珠垂下来,谢逸亭的手也悬在半空。
他忽然想起五年前那个雨天,温晗芯冒雨来找他,浑身都湿透了,只为送他一盒亲手做的点心。
那时候的爱意纯粹真实。
无论是眼神还是心意。
而现在,那双眼睛静得像潭死水。
温晗芯已经带着学生们走进客房,她的背影挺得很直,不卑不亢。
水渍在身后留下一串淡淡的痕迹。
很快就被地毯吸收,就像从未存在过。
谢逸亭无意识地捻动佛珠。
他应该松一口气的。
可胸腔里却涌上一股陌生的情绪,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正在流失,而他抓不住。
距离她要走只有七天了。
经历了这些她的心慢慢放下很多东西。
她准备好好跟孩子告个别。
即使谢念和她没有血缘关系,但好歹养了四年,她早就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了。
温晗芯端着热牛奶站在儿童房门口时,听见了让她心寒的话。
“妈咪,你明天还来接我放学吗?”谢念的声音不大,眼神期待着看向凌清菀的双眼。
“我不想让那个女人接我,看到她就烦。”
“她还偷东西,丢死人了。”
牛奶杯在托盘上轻轻一晃,溅出两滴在温晗芯手背上。
烫,但她没动。
感觉一阵寒意从脊背往上升起,让她不知所措。
“当然啦。”凌清菀揉了揉谢念的头发,余光瞥见门口的身影,故意提高音量,“念儿真乖,妈咪爱你。”
原来......在她不知道的时候,他们母子已经相认了?
那她算什么?
这么多年的抚养教导,就一瞬间消散了?
弹幕又在温晗芯眼前炸开。
我去,这孩子这辈子也就这样了,没良心的东西。
养不熟的白眼狼!
代入一下温晗芯,我恨不得冲进去给她们俩一人一巴掌。
温晗芯深吸一口气,转身想要离开。
没想到这个时候凌清菀打开了门。
“你来啦,是来给念念送牛奶的吧。”凌清菀接过她手上的牛奶。
谢念大喊一声,“我要妈咪喂!”
看都没看她一眼。
“好,我喂你。”清菀意摸了摸孩子的头,笑语盈盈,“念念真乖。”
温晗芯站在原地,看着谢念就着凌清菀的手喝奶。
四年来每晚都是她哄睡的孩子,现在连一个眼神都不肯给她。
她没多说什么,转身走了。
晚点的时候,她打算等谢逸亭结束诵经的时候,跟他说她要离开的事,顺便商谈离婚的事情。
走廊的壁灯将影子拉得很长。
温晗芯走到书房门口,正要敲门,却从虚掩的门缝里看见了令她血液凝固的一幕。
又是这样。
一天之内,到底要把她的心撕成几瓣呢?
谢逸亭站在书桌前,只是盯着她的脸沉默,而凌清菀靠在沙发上睡着了,胸口随着呼吸轻轻起伏。
屋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人。
佛珠被摘下来放在茶几上。
他缓缓俯身。
温晗芯看见他撑在沙发扶手上的手背青筋暴起,像是在极力克制什么,可最终,他的唇还是轻轻落在了凌清菀的唇瓣上。
那么轻,又那么珍重。
她的心一直往下沉。
弹幕比她还激动。
说好的高冷佛子呢?
我真的太心疼温晗芯。
佛珠突然从茶几滚落,谢逸亭猛地直起身,他转头看向门口,眼神还残留着未褪的柔情。
四目相对。
温晗芯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慌乱。
多可笑,她心想。结婚五年,他唯一一次失态,竟是因为被她撞破偷吻别人。
“我......”谢逸亭喉结滚动,像是找出合理的借口,“她睡着了。”
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慌,怕温晗芯生气。
解释是苍白的。
温晗芯想笑,嘴角却像灌了铅。
过了一会,才嘟囔出一句话。
“念儿改口了。”她听见自己说,声音有些哽咽,“他叫清菀妈咪。
想通了之后,她决定到时候提出离婚。
冒出离婚这个念头,她还是忍不住难受,心像是被人用力捏住,细细密密的啃噬痛感席卷全身。
就当这剩下来的十五天是最后的告别吧。
厨房里,温晗芯正在准备谢逸亭的生辰宴。
谢逸亭父子俩昨晚回来了。
要不是生日宴,他们估计还会在山上待一个星期。
“夫人,这些让厨师做就好。”老管家站在厨房门口,看着温晗芯被蒸汽熏红的脸。
确实有厨师在,不用她操心。
只是去年她答应了谢逸亭,今年会亲自给他的生日宴做几个菜。
温晗芯摇摇头,将一缕散落的发丝别到耳后,“就这一次,下次不做了。”
其实他们之间,也确实没有下一次了。
她说着拿起菜刀,开始切冬笋。
忙碌起来反而可以让她放空自己的心,不会再深陷情绪的漩涡中出不来,这些年的付出和委屈只有她自己知道。
谢逸亭修佛,不食荤腥,她便学着做了八样素斋。
她恨自己这样爱他。
越这样想着,手指也越容易颤抖。
刀刃一不小心切入皮肉。
鲜血涌出,顺着案板滴落在她新换的素色旗袍上。
佛堂的门帘微动,谢逸亭走了出来,手持佛珠,眉目如画却淡漠疏离,目光落在她流血的手指上,只微微蹙眉,“小伤而已,别那么紧张。”
弹幕炸开适时出现。
我的天,这狗男人!
他在说什么啊,流血了哎,都不会关心一下吗?
温晗芯还未开口。
门口传来娇呼,带着一丝颤音,“逸亭哥,我手被纸划到了。”
凌清菀举着指尖,上面有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红痕。
如果不仔细看,根本注意不到。
谢逸亭的佛珠“啪嗒”掉在地上,他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,抓住凌清菀的手,“怎么这么不小心?”
老管家匆忙跑去取药,谢逸亭已经掏出手帕,小心翼翼地按住那道根本不存在的“伤口”。
只留她一个人站在厨房里,看着自己仍在流血的手指,突然觉得那血像是从心里流出来的。
弹幕疯狂滚动:
我去!双标现场!
温晗芯血快流干了他看一眼了吗?
凌清菀这个也算伤吗?无语。
四岁的谢念从楼梯跑下来,看都没看温晗芯,径直扑向凌清菀,“林阿姨疼不疼?念儿给你吹吹。”
说着真的踮起脚,对着凌清菀的手指呼呼吹气,又转头对佣人喊,“快去给林阿姨拿创可贴!要卡通图案的!”
温晗芯听着,手上的疼突然蔓延到胸口。
那个她每天哄睡、生病时整夜照顾的孩子,此刻眼里根本没有她这个“妈妈”。
弹幕从来没停过。
白眼狼!
女主白养他四年!
是演的?我刀呢!
温晗芯的伤口还在流血,染红了按着的纸巾,她默默走到水池边,用冷水冲洗。
冰凉的水冲在伤口上,疼得她眼眶发热,但她咬着唇没出声。
血混着冷水冲进下水道。
像她五年的婚姻,悄无声息地流走。
谢逸亭在给凌清菀贴创可贴,头也不抬地说,“晗芯,清菀手伤了,你去做饭吧。”
温晗芯关掉水龙头。
“我......”她声音发抖,眼睛也发酸,“我的手也伤了。”
谢逸亭这才看向她,眉头微皱,“你不是已经包扎好了吗?清菀从小怕疼,你别计较这些。”
原来不在乎一个人,真的可以变成盲眼耳聋的人。
眼里心里只剩那个他在乎的女人身影。
凌清菀适时地“嘶”了一声,娇弱的嗓音直接吸引住谢逸亭的目光。
他立刻转回去握住凌清菀的手,“还疼?要不要去医院?”
去医院吗?
恐怕下一秒就要好了。
温晗芯看着这一幕,突然觉得荒谬至极,她转身回到厨房,关上门,终于撑不住,滑坐在地上。
手指的伤口很深,血止不住。
她胡乱又扯了块干净毛巾按住,眼泪却比血先滴下来。
五年了,她以为只要足够耐心,足够温柔,总有一天能融化谢逸亭这块冰。
可现在她明白了,他不是冰,只是对她冷而已。
她终于看清了。
佛堂里供奉的从来不是神明。
而是他藏在佛珠下的,那颗偏爱别人的心。
门外传来谢念的笑声和凌清菀的娇嗔,还有谢逸亭低沉的应答。
多么和谐的三口之家啊,而她,像个多余的摆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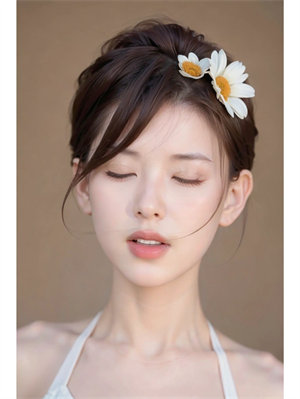 >
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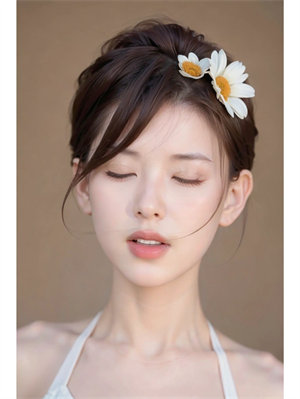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