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要是,他真的有些承受不了荣妄的嘴了。一想到,被女婿像训孙子似的训一辈子,他就觉得也不是非攀荣妄这根镶了金的高枝。裴桑枝秀眉一扬,伸出手,指了指脑袋,语气格外真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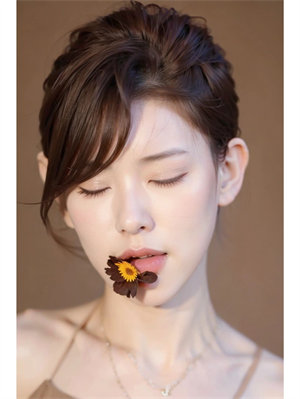
主要是,他真的有些承受不了荣妄的嘴了。
一想到,被女婿像训孙子似的训一辈子,他就觉得也不是非攀荣妄这根镶了金的高枝。
裴桑枝秀眉一扬,伸出手,指了指脑袋,语气格外真诚:“父亲,您这里面一半是面,一半是水,摇一摇就变成了浆糊吧。”
“您怎么有勇气挑剔上荣国公的?”
“是祖父给您的吗?”
“是您亲口说荣国公极得陛下宠溺,就连皇子公主们也略有逊色,不论行至何处,皆被人捧着敬着。”
“倘若这话传到荣国公耳朵里,怕是要在侯府门前摆开阵仗,骂个三天三夜都不带重样的。”
永宁侯表情难看:“你我父女之间的私语,旁人怎么会知。”
裴桑枝勾唇,似笑非笑:“不怕一万,就怕万一。”
“另外,女儿觉得父亲可能错估了祖父的实力。”
“即便有祖父撑腰造势,永宁侯府在荣国公府面前依旧不堪一击。”
永宁侯气的吹胡子瞪眼,不忿的争辩:“纵是他权势滔天富贵逼人,难道还能凌驾于皇室之上?”
“失了陛下的恩宠与荣老夫人的庇佑,他眼下的风光终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昙花罢了。”
裴桑枝闻言,嘴角笑意骤然消散,垂眸盯着洒在案几上的光点,声音浸了霜,掷地有声:“父亲慎言。”
“您这般口无遮拦,是要拖着整个裴家去死?”
“你我合谋利益,就在同条船上,船沉了对谁都没有好处。女儿不想看您像母亲那样犯癔症,拖后腿,平白碍事。”
“您刚才那番话,随随便便被编排一番,就成了父亲有不忠、不臣之心,巴不得陛下和荣老夫人短命。”
永宁侯怔在原地。
裴桑枝心下不耐愈盛:“您浸淫权势半生,见惯尔虞我诈、算计倾轧,合该更小心敏锐,谨慎善思,怎的这般……”
说到此,不由得加重语气:“这般愚钝轻狂!”
“如果眼蒙尘翳,耳塞棉絮,那就捂的彻底些,做个十足的蠢货,反倒安全。”
永宁侯下不来台。
他女儿到底是个什么混账玩意儿,竟然这么不给他面子!
指着他的鼻子骂他,跟在大庭广众之下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,有何区别!
“为父绝无此意!”永宁侯咬牙切齿。
裴桑枝蹙眉蹙的更紧了,脱口而出:“那些朝堂上的政敌豺狼攻讦撕咬你时,可会细究你究竟存没存那份心思?”
永宁侯闻言瞳孔骤然收缩,喉结艰涩滚动数下,终是心虚的息了声,半句辩白也未能出口。
“父亲。”裴桑枝拔高声音。
永宁侯瓮声瓮气:“做甚?”
“还没骂够吗?”
简直倒反天罡!
裴桑枝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望着永宁侯,旋即,推过去一盏早已没了热气的茶:“父亲,您还是先饮盏冷茶醒醒神吧。”
“等这心头邪火散了,您那被怒气冲散的清明神智,总能归位了吧。”
永宁侯:他听懂了,裴桑枝又在阴阳怪气他。
“你有话直说。”
裴桑枝叹了口气,无奈闭了闭眼,再睁眼,已是一片平静:“您把陛下的口谕当作耳旁风了吗,还是说已经做好准备迎尚宫局女官入侯府了?”
“父失公允,母丧慈心,兄悖人伦……”
“您恭听陛下口谕,总要有所作为啊。”
果然,人不能动怒,动怒会让人变蠢。
永宁侯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大鹅,涨红着脸,手指死死抠着雕花扶手,嘴硬道:“为父心里有数。”
“做事情,总得按部就班,慢慢来。”
“正因为为父看重你,这才先将你唤来,指点教导你。”
凉茶里清清楚楚的映照着永宁侯被戳中心窝子的狼狈。
裴桑枝干巴巴道:“女儿实在是太荣幸了呢。”
“敢问父亲,指点完了吗?”
“容女儿提醒一句,您还答应了荣国公和小李公公,要亲手叠元宝、剪纸钱、做纸扎,去惊鹤兄长的坟头儿烧了。”
“扎纸马香幡、亭台楼阁,很费功夫的。”
永宁侯胸口憋闷的更难受了,像是梗着块烧红的炭,呼吸吞咽间都带着股铁锈味,心下忍不住想,究竟是什么泼天的富贵和迷人眼的利益,值得他时时处处做孙子!
“桑枝,我是你父亲。”
裴桑枝直截了当:“父亲这是在责怪女儿方才与您争执么?”
“有争执才恰恰说明,你我父女缘分未绝,否则,女儿可以像漠视母亲一样,视父亲如无物。”
“您是想做永宁侯府这艘百年航船的掌舵人,还是想效仿庄氏,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门心思混吃等死?”
“父亲,想想你我的光明未来啊。”
永宁侯又可耻的动摇了。
他总觉得,裴桑枝说话,既带着刺,又裹着蜜。
一面,让他恨的牙痒痒。
一面,又让他心驰神往。
“父亲日后若见女儿有行差踏错之处,只管严加训诫便是。”裴桑枝适时的递了个妥帖的台阶,全了永宁侯的颜面,让他有机会顺势下来。
永宁侯见好就收,顺势转开话锋,捋须沉吟着说道:“依你之见,为父此番当如何做,方显忠忱?”
裴桑枝眼睑颤了颤,笼统道:“只要让陛下看到父亲的决心便好。”
“至于确切如何做,女儿不便多言。”
“庄氏和裴临允,终归是女儿血脉相连的至亲。”
永宁侯是真心求教吗?
不,又是意在祸水东引。
“女儿先行告退,回听梧院了。”
“待父亲思虑周详,做好决断,再差人唤女儿前来。女儿定当尽心,教父亲叠金元宝、剪冥纸钱,做纸扎。”
一语毕,永宁侯更心烦意乱:“滚!”
裴桑枝睫毛微微颤动,在眼睑投下一片阴影。
眉眼低垂,脑海里浮现出裴驸马所说的关于裴惊鹤的种种,几番思量间,心中已转过千百个念头。
从种种迹象来看,永宁侯对待裴惊鹤的态度,全然不见丝毫慈爱之心。
难不成,裴惊鹤受其母所累,永宁侯恨屋及乌?
亦或者是……
永宁侯见裴桑枝如木雕泥塑般僵立原地,不由眉头紧蹙,怒从心起,厉声喝道:“还不速速离走!”
跟裴桑枝说话说多了,容易短命!
裴桑枝抬头,郑重其事道:“父亲,女儿心中有一言,思忖良久,如鲠在喉,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
长得丑,想的美。
呵,用畜生来形容裴临允都是在侮辱畜生二字了。
“我果然没看错你,你就是心机深沉,想挟恩图报!”
“裴桑枝,你可真龌龊!”
裴桑枝如坠深渊,用看陌生人的眼神凝视了裴临允片刻,旋即,猛的上前,抬手,使上浑身力气,狠狠的扇在裴临允脸上,先发制人,凄厉反问:“三哥,你还是不是人。”
终于是对称了。
永宁侯扇巴掌怎么老是只扇一下。
对称美,懂不懂!
裴临允脑中轰鸣作响,火辣辣的痛感后知后觉涌上来,嘴角似有铁腥味溢出。
她怎么敢!
她怎么敢的!
“公子。”
“四姑娘。”
裴临允和裴桑枝的婢女惊呼出声。
“权当我过去的真心饲了野犬!”
裴桑枝下颌微抬,唇边凝着讥诮的冷笑,神情里尽是决绝和憎恶。
而后,伸手抄起檀木矮几上的另一只白瓷碗,重重砸在地上。
碎片飞溅。
裴临允怔愣,连躲闪的动作都忘记了。
些许碎瓷划过裴临允的面颊,带起串串血珠。
“我龌龊?”
“我挟恩图报?”
裴桑枝看着裴临允肿胀的左脸,淌血的嘴角,心下是汹涌的快意,继续刺激:“真正连畜生都不如的是谁!”
“从此以后,你我也不必兄妹相称了。”
她说过,裴临允这把刀好用的紧。
终于无需在裴临允面前演逆来顺受的戏码了。
“还有……”裴桑枝勾勾唇,晃了晃被软布包扎着的手腕,恶意满满:“我奉劝裴三公子一句,日后羞辱我时,最好再三斟酌言辞。”
“你我一母同胞,而且,我用血肉救过你。”
“说句难听的,你的身体里也流窜着我的血。”
“看清楚了吗,这才是挟恩图报该有的倨傲和自得!”
裴桑枝嗤笑着睨了裴临允一眼,踩着满地的狼藉,扬长而去。
素华看傻了。
这还是那个只会无声落泪,任人欺凌的四姑娘吗?
四姑娘掌掴三公子,她敢说,都没有人敢信。
眼见裴桑枝越走越远,素华迅速朝着裴临允欠了欠身行了一礼,匆忙跟上。
此刻,在掠过庭院洒扫的下人时,裴桑枝脸上的悲愤和凉薄已化为凄楚和哀痛。
她掌掴兄长,非她无情无义,是无可奈何。
“四姑娘。”
“四姑娘。”
素华急切的的呼唤碎在风里,裴桑枝的脚步越来越快,最后攥住裙裾往上一提,三步并作两步,闯进了折兰院。
忙忙碌碌一整夜的永宁侯浑身疲乏,正躲在书房偷闲小憩,忽听院里又起嘈杂,心口一堵,如遭重锤,眉头不受控制的紧紧皱起,烦躁的掀起身上的狐裘,站起身来,瓮声瓮气道:“院外何事喧哗!”
语气不耐,似钝刀磨石。
就不能让他得一刻清静吗?
喝问声让庭院里的喧哗止了一息。
须臾后,带着哭腔的请罪和“扑通”下跪的声音同时出现。
“女儿有错,请父亲责罚。”
没头没尾的一番话,让永宁侯的心高高悬起。
若是不小心请回来了……
他简直不敢想象自己的日子会过的多水深火热。
在他眼里,驸马爷从不是靠山,而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存在。
庄氏不敢耽搁,先是匆匆吩咐下去,而后才明知故问道“桑枝不会是去了佛宁寺吧?”
“她……”庄氏佯作焦急:“她怎能如此不懂事,去惊扰驸马爷的安宁。”
永宁侯冷笑一声:“那你怎么不自省下,她已经认祖归宗月余了,怎的至今仍对侯府的内情还是两眼一抹黑。”
庄氏语塞。
又埋怨上她了。
当初,不是他们商议过后决定眼不见为净的吗?
“是妾身之过。”庄氏僵硬的岔开话题:“眼下,当务之急是赴荣老夫人的茶会。”
“急躁则生乱,侯爷先静静气。”
永宁侯:静静气?根本静不了一点。
永宁侯和庄氏战战兢兢地登门了。
既是气的,也是怕的。
暖阁。
“晚辈给荣老夫人请安。”永宁侯和庄氏规规矩矩的行礼。
荣老夫人执定青瓷盏,徐拂雪沫浅啜半口,垂目缓言:“茶会雅事,何必拘形束礼?”
盏底轻叩檀案,话音略顿,唇角微抬,又添一句:“今稍顷另有贵客临门,且待片时。”
话说的平易近人,然,通身却是不怒自威。
首当其冲的永宁侯和庄氏,更觉威仪惊人,愈发不敢放松警惕。
直到,荣老夫人抬抬手,抛出句“坐吧。”,永宁侯和庄氏才抬起头。
“咚、咚、咚。”
沉闷的声音犹如鼓点般响起。
永宁侯小心翼翼循声望去,但见一袭孔雀绿长袍的荣妄屈指,一下又一下的敲击着紫檀木桌沿:“裴侯爷心底没有尊卑了吗?”
“还是说,本国公在裴侯爷眼里如同无物,裴侯爷欺本国公年少!”
艳丽又冷冽,嘴角还噙着讥嘲。
永宁侯的心颤了又颤。
这活祖宗,怎么跟吞了炮竹似的。
荣妄根本不给永宁侯应对的时间,继续道:“本国公是陛下亲封的世袭罔替的荣国公,裴侯爷这般目中无人,是要不敬圣意,还是要当陛下的主子。”
“你们要谋反不成?”
荣妄是真的恨极了永宁侯。
但,裴惊鹤功劳的遗泽却洒在了永宁侯身上。
世人一提,永宁侯的原配长子于他有救命之恩。
子死,父沾光。
永宁侯一咬牙不顾颜面,直接“扑通”一声跪行大礼:“荣国公明鉴,下官忠心耿耿,日月可昭,绝不敢有一丝一毫的不敬、不忠,亦不敢轻忽您。”
庄氏有一瞬间的傻眼。
活了半辈子的侯爷,就这么干脆又窝囊的跪了?
说好的男儿膝下有黄金呢,侯爷的膝盖骨怎么比她还软。
回神后,有样学样,亦跪伏在地。
荣老夫人修剪圆润干净的指甲划过青瓷盏上的花纹,眼神晦暗不明的掠过墙角的长颈大花瓶。
真想如年轻时,简单粗暴的抄起花瓶砸向装模作样的永宁侯。
罢了,青瓷盏和长颈花瓶都太贵了些,碎在永宁侯身上不值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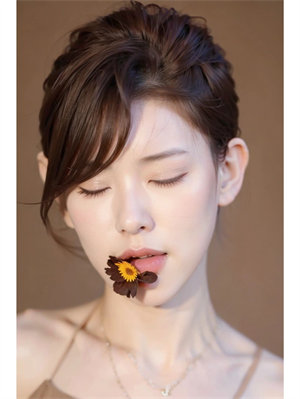 >
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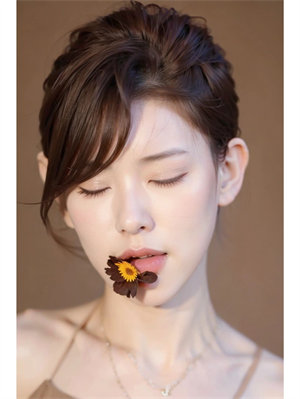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